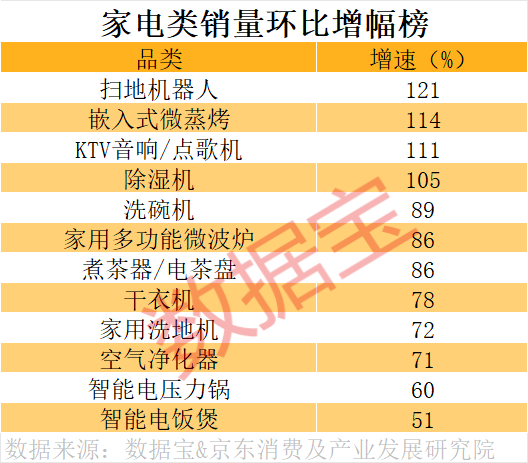公众号记得加星标,第一时间看推送不会错过。
回望过去几十年,英特尔曾是芯片行业最活跃的买家之一:它先后买下DEC和英飞凌无线业务,进军移动芯片市场;收购了McAfee,试图将安全能力嵌入硬件;买下了Wind River,试图控制嵌入式系统生态;斥资收购 Altera,希望借FPGA补足数据中心与异构计算能力;收购Mobileye、Habana、Movidius、Moovit,从自动驾驶到AI加速器,几乎无所不投;连模拟代工厂 Tower 都想纳入麾下,意图补足工艺谱系。
但时至今日,这些曾经被纳入“自有平台版图”的业务,要么被出售、要么被分拆独立、要么被推向ipo。它曾经想要构建的“软硬通吃、平台闭环”的庞大帝国,现在正在被自己一砖一瓦地拆解还原。
当 AI 的巨浪推着整个半导体行业进入“烧钱-整合-再融资”的循环,这个芯片巨头选择了一条更激进的路径:把几乎所有“非核心、非代工、非 x86/AI 基础盘”的业务能卖就卖、能分立就分立。这是英特尔在产业转折点上的“降维自保”式选择――主动收缩战线,压缩组织惯性,腾挪财务杠杆,用资源换取在主航道上的再战机会。
一张“20年剥离清单”:
英特尔退出了哪些业务?
由于英特尔的历史悠久,过去二十年,它通过多轮业务扩张构建了庞大的平台体系,也在数次战略转型中果断撤离了不再契合核心战略的板块。鉴于英特尔收购与出售数量众多,本文仅列举部分关键性的事件,以管窥英特尔如何一步步“瘦身”、回归主线。
1
移动市场,三次战略撤退
在PC时代所向披靡的英特尔,却在移动芯片领域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战略性撤退。
第一场撤退:出售XScale,告别ARM阵营。早在2000年代初,移动互联网与嵌入式市场快速发展,英特尔也试图布局 ARM 阵营。1997年,英特尔收购了DEC的相关业务(主要是为获得其Alpha架构、strongARM产品和一些芯片设计资产),因此StrongARM处理器归入英特尔旗下。英特尔在继承StrongARM的基础上,推出了自己的ARM家族处理器品牌――XScale。XScale属于ARMv5架构,主要应用方向包括:智能手机(如黑莓、Palm Treo)、网络与通信设备、工业控制与消费级嵌入式终端。
在2000�C2005年间,XScale 是英特尔在非x86领域最主要的产品线。尽管XScale具备市场潜力,但英特尔最终选择在2006年6月将XScale业务整体出售给Marvell,作价6亿美元。
XScale处理器的PXA255系列
(来源:wikipedia 作者 Raimond Spekking /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
这是英特尔第一次大幅退出移动SoC赛道。彼时,英特尔正面临来自AMD的挑战(Athlon 64 横扫桌面市场),亟需专注x86主业反击。再加上XScale属于Arm架构,与英特尔生态“主干”脱节,难以共享研发/制造/软件资源。彼时智能手机尚未全面崛起(iphone尚未发布),XScale虽有应用但营收占比小。英特尔就这样放弃了ARM阵营的“船票”,坚定押注 x86 与自有平台战略――这个选择成就了桌面/服务器的辉煌,也埋下了移动端缺席的遗憾。
Marvell接盘后继续深耕Arm SoC,这也成为Arm阵营全面崛起的转折点之一。随后几年内,Arm架构迅速崛起,苹果自研A系列芯片、高通Snapdragon横扫安卓阵营,Arm逐渐成为移动市场主导架构,英特尔渐渐失去移动芯片市场。
第二撤退:Atom的失败。进入21世纪10年代,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PC市场增速放缓,英特尔意识到不能仅仅依赖PC处理器业务,决定重返智能手机市场。英特尔在 2008 年推出了x86方案的凌动(Atom)处理器,专门针对上网本设计,它采用了顺序执行设计,transistor数量少,功耗低,发热量小,非常适合轻薄设备。Atom处理器迅速成为上网本的主流芯片,帮助英特尔在当时占据了这一新兴市场的主导地位,于是英特尔也试图将 Atom处理器推广到手机和平板领域。
尽管英特尔在处理器方面有优势,但在移动通信领域,它缺少手机处理器的外围关键配套,比如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和电源管理等。于是,在2010 年,英特尔以 14 亿美元收购英飞凌(Infineon)的无线解决方案事业部。英飞凌的无线解决方案事业部在基带芯片领域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份额,特别是为包括苹果 iPhone 在内的全球高端手机制造商提供无线移动通信设备。收购英飞凌的这部分业务,能够直接弥补英特尔在移动互联技术上的空白,补足其“互联联通能力”。这次收购,是英特尔再次强力进军智能手机市场的标志。
然而,Atom 在移动市场遭遇了ARM 架构处理器的强大挑战。ARM 处理器在功耗效率和集成度上更具优势,且拥有庞大的生态系统和大量的应用程序支持。尽管英特尔投入了大量资源,甚至对 OEM 厂商提供补贴以推动 Atom 手机和平板的上市,但市场对搭载 Atom 的移动设备的接受度并不高。
面对巨大的亏损和与 ARM 的差距,英特尔在 2016 年左右,逐步退出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Atom处理器市场,并终止了多款针对移动设备开发的 Atom 芯片项目(例如 Broxton和Sofia)。Atom处理器虽然未能成功在智能手机和平板市场与 ARM 竞争,但它并没有消失。英特尔通过战略调整,使其在物联网、边缘计算和嵌入式系统等细分市场找到了新的生命力,并持续发挥其低功耗和 x86 兼容性的优势。
(图源:intel)
第三撤退:Modem折戟,告别移动市场。除了处理器,英特尔也试图从通信层面切入移动市场。收购英飞凌无线部门后,英特尔推出XMM系列基带,并在2017�C2019年间,借苹果与高通专利纠纷之机,成为iPhone X到XS期间的唯一基带供应商。
然而,英特尔基带一直存在三大短板:一是与高通的同代基带相比,英特尔的XMM系列经常延后6�C12个月,5G进展尤为缓慢;二是高通在基带市场长期占据压倒性市场份额,且持有大量标准必要专利(SEP),高通的客户绑定策略(SoC + Modem +封装)使得英特尔难以打入安卓阵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苹果与高通专利诉讼战,2019年4月,苹果与高通突然和解,并签下多年基带芯片协议 + 60亿美元付款,同日英特尔宣布退出5G 手机基带业务。最终2019年7月,英特尔将整个Modem业务打包卖给苹果,交易金额约10亿美元,成为其移动芯片征途的终点。实质上,英特尔被苹果“扶上马、送出城”,但也只是陪跑与战略谈判的工具人。
XScale的放弃让其失去了ARM生态门票,Atom的失败揭示了架构延续的局限,Modem业务的终止则是生态与整合能力欠缺的集中体现。虽然英特尔在PC与服务器领域仍占据主导,但移动端的缺席,已成为其芯片史上一段无可回避的空白。
2
软件领域的收购与卖出:
McAfee和Wind River
在“软硬一体”成为业界热词的年代,英特尔曾试图通过两次关键性收购――McAfee 和 Wind River――将安全与嵌入式软件深度绑定硬件产品,以期打造端到端的芯片平台优势。
2009年,英特尔以 8.84 亿美元收购实时操作系统(RTOS)厂商 Wind River,希望其嵌入式系统能力可支撑英特尔进军工业与边缘计算设备市场。
2010年,英特尔又以高达 76.8 亿美元收购全球第二大网络安全厂商 McAfee,希望以“芯片级安全”为核心,构建可信计算生态。
当时看,两笔收购均有明确战略逻辑:Wind River 对应“嵌入式 + IoT + 工业控制”;McAfee 对应“安全 + 硬件信任根 + 平台整合”。但这两条软硬协同路径,最终都没能跑通。
Wind River是RTOS领域的标杆,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等高可靠场景。英特尔希望借助Wind River,与自家的低功耗SoC(如Atom)绑定,打通从设备端到数据中心的“端到云”平台链路。但现实是:英特尔 Atom 系列在嵌入式和工业市场竞争力不足,难敌NXP、TI、ST等ARM阵营;IoT市场高度碎片化,单点利润低、生态复杂,不适配英特尔擅长的大平台逻辑;RTOS本身虽强,但无法反向驱动芯片销量。最终,“软件 + SoC + 云” 的产业闭环并未形成。2018年4月,英特尔将Wind River出售给私募基金TPG。
英特尔收购McAfee的初心,是把安全能力下沉到芯片与固件层,实现从硬件到操作系统再到应用层的全面信任链,从而构建差异化的可信平台。但协同效果远不如预期:McAfee 主战场在桌面、移动、服务器平台,其产品线与英特尔芯片并无天然耦合;缺乏杀手级应用场景推动“硬件安全”向终端渗透,软硬之间无法形成闭环;McAfee 自身也处在从传统杀毒向网络安全转型的过渡期,业务调整与英特尔的目标节奏不一致。2016年,英特尔将其 51% 股权出售给TPG,保留49%,McAfee成为一家独立公司。
但是,无论是McAfee还是Wind River,并非没价值,而是与英特尔的协同不好,不适合留在英特尔:McAfee在2020年重返纳斯达克上市,市值最高一度超过 100 亿美元,2021 年被另一PE巨头Advent International私有化退市。Wind River 在2022年被汽车电子巨头 Aptiv以42亿美元收购,成功“二次退出”。
Wind River历史(来源:该公司官网)
对于像英特尔这样的芯片厂商而言,软件投资是否成功的关键不在“好不好”,而在“能否形成生态优势”。无论是嵌入式系统还是安全平台,如果不能帮助英特尔的芯片获得更多设计赢单、出货规模与利润空间,那它就只是一项“财务投资”,而非战略引擎。
3
NAND现实的败退和Optane愿景的崩塌
在存储领域,英特尔曾试图从两条路径突围――一是参与NAND这类主流市场以实现规模效应,二是自研Optane开辟“第三类存储”以构建技术护城河。
2020年10月,英特尔宣布把NAND闪存业务、大部分 SSD 产品线(包括数据中心级别)、中国大连工厂(原Fab 68)出售给SK海力士,交易金额约90亿美元(后因汇率调整,实际接近70亿美元),2022年末完成剩余资产转让(包括大连工厂)。
这次出售,背后逻辑可以归纳为“三个不如意”:1)NAND市场长期被三星、SK海力士、Kioxia、美光等厂商垄断,英特尔难以突围。2)盈利难维持:产品利润率低,规模效应不足,成为拖累整体财报的业务单元。3)技术代际落后:大连工厂的制造工艺落后于一线大厂,研发投入回报低,与其烧钱硬撑,不如卖给 SK hynix 实现“有价退出”。
比NAND更让英特尔痛惜的,是其自主研发、寄予厚望的Optane(傲腾)产品线。Optane基于3D XPoint技术,主打“存储级内存(SCM)”概念,定位于打破传统“DRAM + NAND”二分架构,成为第三类介质,在性能、容量和持久性之间提供新平衡。它曾被视为英特尔“CPU + 存储 + 软件栈一体化平台战略”的重要支点,是软硬协同的代表作。但最终,它也走向了终点。2022年,英特尔正式宣布终止Optane产品线,宣告这场技术理想的失败。
傲腾(来源:intel官网)
Optane终止的背后也有着诸多痛点。第一,成本劣势:Optane基于相变存储(PCM)工艺复杂、良率低,成本几乎接近DRAM,价格优势不明显。第二,市场教育成本高,而多数客户习惯于“DRAM + SSD”传统结构,迁移成本巨大。Optane本应是打通“从芯片到底层存储架构”的象征性工程,然而,最终却未能撼动主流市场结构――不是性能不行,而是“不够便宜、也不够刚需”。
4
汽车市场:
Mobileye二次上市,关闭汽车业务
英特尔在过去十年对汽车智能化下注颇深,从Mobileye到Moovit,从ADAS芯片到出行平台,曾试图打造一个跨越硬件、平台与数据的“车载帝国”。但多年投入之后,这场豪赌正在悄然收场。
在2015年左右自动驾驶汽车技术蓬勃发展的初期,英特尔对汽车的押注很大。2017年3月13日,英特尔宣布以153亿美元收购了该无人驾驶技术公司Mobileye,这成为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最大金额收购案。
Mobileye当时是全球最成熟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厂商之一,其EyeQ系列芯片广泛搭载于宝马、奥迪、特斯拉等车型。英特尔试图借此打入车规级计算、感知融合与智能驾驶平台层,与英伟达、高通一争高下。
2020年,英特尔再斥资约9亿美元收购出行平台公司Moovit,希望以MaaS(出行即服务)平台为抓手,推动Mobileye向“数据+平台+服务”的纵深整合迈进。
Mobileye虽在技术路线上不断升级,从ADAS迈向L3+自动驾驶,并推出REM高精地图、Robotaxi平台,但它也面临严峻竞争格局:英伟达、高通等芯片巨头相继发布车载SoC平台,与Mobileye正面交锋;中国市场上,黑芝麻智能、地平线等新兴公司加速迭代,占据本土车企合作高地;Mobileye虽表现活跃,但与英特尔整体产品栈协同程度不高,生态粘性弱、营收并表复杂。
2021年12月,英特尔宣布推动Mobileye独立IPO,于2022年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虽仍保留多数股权。外界普遍的解读为英特尔意图淡化汽车芯片业务。Mobileye的股价从上市至今已经累计下跌约45.6%。2025年7月,英特尔通过二次发行出售Mobileye 5750万股A类普通股,为资产负债表增加了约9.22亿美元资金。
然而在2024年1月的CES大会上,英特尔又宣布收购Silicon Mobility SAS――一家专注于为电动汽车(EV)智能能源管理提供SoC的无晶圆厂芯片和软件公司。彼时英特尔对于汽车业务还是很看重的。Silicon Mobility 的SoC 采用业界领先的加速器,专为能源传输而设计,并与高度先进的软件算法共同设计,可显著提高车辆能源效率。Silicon Mobility 的技术组合将拓展英特尔在汽车领域的业务范围,从高性能计算扩展到智能可编程功率器件。此次收购尚需获得必要的批准。
不过今年6月份,英特尔传出决定关闭客户端计算事业部(Client Computing Group)下的汽车业务。英特尔在回应媒体时表示,这是其“聚焦核心客户端与数据中心产品组合”战略的一部分。言下之意是,汽车这条支线,已不再承载主航道压力。这标志着英特尔对“泛汽车计算”的全面收缩:既放弃了自主布局汽车SoC的尝试,也将Mobileye推向独立资本轨道,最终回归“PC + 数据中心”的盈利主心骨。
在高度定制、周期漫长且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英特尔用一次完整的进入―深耕―退出,完成了它在这个市场的一次战略闭环。
5
拆分独立多个业务:
Altera、NEX、RealSense、投资
最近两年来,面临股价大跌和财务承压的困境下,英特尔内部正在大张旗鼓的进行深度业务剥离与结构重构。
2025年1月,英特尔宣布计划将其全球风险投资部门英特尔投资(Intel Capital)拆分为一个独立基金。英特尔投资成立于 1991 年,是全球领先的企业风险投资公司之一,管理着超过 50 亿美元的资产。30 多年来,英特尔投资已投资超过 1800 家公司,并投入超过 200 亿美元的资金。仅在过去 10 年里,该公司就通过投资塑造计算未来的关键领域(包括硅片、前沿技术、设备和云)的早期初创企业,如Ayar Labs,创造了超过 1700 亿美元的市值。预计独立运营将于2025年下半年开始,届时英特尔投资将以新名称运营。
RealSense 作为英特尔内部孵化的感知计算技术,曾一度用于AR/VR、机器人、智能终端等场景。2025年1月,英特尔宣布将 RealSense 作为独立初创公司剥离,交由英特尔投资(Intel Capital)控股。2025年7月11日,RealSense Inc. 正式完成剥离,并完成 5000万美元融资,将聚焦机器人视觉等B端场景,寻求自主成长路径。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英特尔收购了视觉处理单元 (VPU) 制造商 Movidius。Movidius 的 VPU 技术被整合到英特尔的 RealSense 摄像头和边缘 AI 解决方案中,用于增强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推理能力,尤其适用于无人机、VR/AR 和智能安防等应用。
图源:RealSense
2025年5月,英特尔将其Altera业务的51%出售给全球领先的技术投资公司银湖资本,英特尔将拥有Altera业务剩余的49%股份。英特尔于2015年斥资 167亿美元收购FPGA厂商 Altera,希望借其可编程芯片能力补齐数据中心、通信与汽车芯片拼图。但十年之后,Altera未能成为想象中的“xPU补充引擎”,反而拖累英特尔整体财务表现。2024财年,Altera实现营收 15.4亿美元,但却录得 6.15亿美元运营亏损,利润率持续承压。
2025年7月底,据The register报道,英特尔正将其网络和边缘计算事业部(NEX)剥离为独立业务,英特尔将作为独立业务的基石投资者,并寻求外部资本。这一分拆消息凸显了陈立武重组公司的力度之大。英特尔的NEX事业部(网络与边缘计算)曾是“云-边-端”协同战略的重要一环,主攻5G网络、边缘服务器、通信基础设施等场景。2024年9月,NEX 被整合进客户端计算集团(CCG),暗示其边缘定位已弱化。
为什么英特尔必须“瘦身”?
从2006年卖掉XScale、到2016年剥离 McAfee、再到 2021�C2022 年清仓 NAND/Optane、2022年分拆并再上市Mobileye,以及2025年相继出售Altera多数股权、把NEX(网络与边缘)独立出去、让英特尔Capital与RealSense走向市场――英特尔正在加速“瘦身”。这些操作并非简单“甩包袱”,而是英特尔在资源有限、赛道激烈的背景下,对自身组织与资本结构的深度优化。
英特尔曾经是“端到端平台公司”:从 CPU、GPU、网络、存储、调制解调器、车载、AI、软件、安全……但这些板块之间的资本周期、技术演进、客户结构完全不同,牵引组织效率。
接下来,英特尔要继续搞制程(Intel 18A/14A 及后续节点)+ 代工(IFS)意味着连续多年、千亿美元量级的重资产投入,资本开支过重,必须把非关键资产外迁。剥离=现金回流+亏损切割+让独立公司自融。
AI与代工窗口期很短,需要“all in”。在AI 基础设施芯片(CPU/GPU/加速器)、CPO、先进封装、系统级设计、EDA 等领域,英特尔正在与台积电、三星、AMD直接对线。英特尔必须在2�C3个“真正能赢”的高地上集中火力。
在AI领域,2019年,英特尔以约20亿美元收购以色列AI芯片新锐 Habana Labs,获得其两大核心产品线:面向数据中心AI训练的Gaudi和面向边缘/云侧推理场景的Goya。Habana补充了英特尔自研Nervana后在AI芯片方面的架构多样性,形成训练+推理一体的算力栈,作为对抗英伟达和AMD GPU主导地位的重要支点。
在代工方面,2021年,英特尔宣布以约44亿美元收购以色列模拟晶圆代工厂Tower Semiconductor,意图借助其模拟/电源工艺与客户资源,扩展自家代工服务版图。该收购因监管原因于2023年终止,但双方随后达成合作协议:Tower将使用英特尔新墨西哥州工厂的300mm晶圆制造能力;双方共建产线,每月新增超60万张光刻层产能,专供模拟/混合信号工艺;实质上以“产能绑定”方式达成软性并购效果,形成客户协同与平台联动。
英特尔在重建什么?――
“3根主线+ 2个杠杆”
经历多次战略收缩与结构重组后,英特尔正以一种更具聚焦感与资本效率的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增长轨迹。在陈立武的主导下,这家芯片巨头不再执着于“全能整合”,而是在厘清资源边界后,重建三条核心主线,同时借助两大外部杠杆提升战略撬动力,以更聚焦、更轻盈的姿态,去搏未来更确定的主航道胜率。
3根主线当中,第1根是x86平台,在客户端(PC)和服务器端(数据中心)领域,x86架构仍是英特尔最稳固的护城河。
第2根主线是AI,面对NVIDIA在AI训练与推理领域的统治地位,英特尔选择构建一套更具开放性与性价比的“异构算力堆栈,包括GPU/加速器 + Gaudi + FPGA 合作模式。AI不是英特尔的舒适区,但它必须押注,否则未来就没有平台意义。
第3是IFS + 先进封装。IFS(Intel Foundry Services)是英特尔最重资产、也最具有地缘杠杆性的板块。尤其在AI芯片日趋复杂、Chiplet架构盛行的背景下,封装能力已成为产业新制高点。英特尔希望借IFS不仅服务自己,更成为美国制造的代工核心。
两个杠杆是指资本杠杆和政策杠杆,从内部重构到外部借力。
资本杠杆方面,拆分 Altera、剥离 NEX、独立 RealSense、推动 Mobileye IPO、让 Intel Capital 自主募资……英特尔正在用所有能动用的资本工具,把长周期、重资源、协同弱的业务“甩出去”,以获得更高资本效率和更轻资产的运营方式。
政策杠杆方面,英特尔借助 CHIPS Act(美国芯片法案)、欧盟补贴政策以及国别安全审查制度,英特尔正将“美国制造 + 安全可信”的标签转化为新的订单与溢价――成为“去C化”和“去T化”的安全选项。尤其在先进封装和AI芯片代工等敏感产业链节点,英特尔逐渐占据政策配置优势。
结语
从“什么都想做”到“只做能赢的”,英特尔的买入与卖出,再次印证了一句亘古名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英特尔正在把“过去 20 年里为了自我平台化而拓展出来的业务”逐步交还给市场:或交给PE去重塑经营效率,或交给产业巨头去整合供应链,或直接交给资本市场去估值与融资。英特尔留下的,是三张牌:x86、AI、代工。而它接下来的命运,将取决于这三张牌能否重新组合出胜率――在一个由TSMC、NVIDIA、Arm主导的新世界里。
从“全平台巨无霸”转型为“聚焦硬核制造 + 开放生态”的公司,决策、节奏、容忍度都需重构。过去英特尔靠全栈绑定增强黏性,未来更多靠产品力 + 代工服务水平说话。转型仍在进行,挑战远未结束,让我们继续观察这场芯片巨头的自我博弈。
*免责声明:本文由作者原创。文章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半导体行业观察转载仅为了传达一种不同的观点,不代表半导体行业观察对该观点赞同或支持,如果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半导体行业观察。
今天是《半导体行业观察》为您分享的第4112期内容,欢迎关注。
加星标第一时间看推送,小号防走丢
求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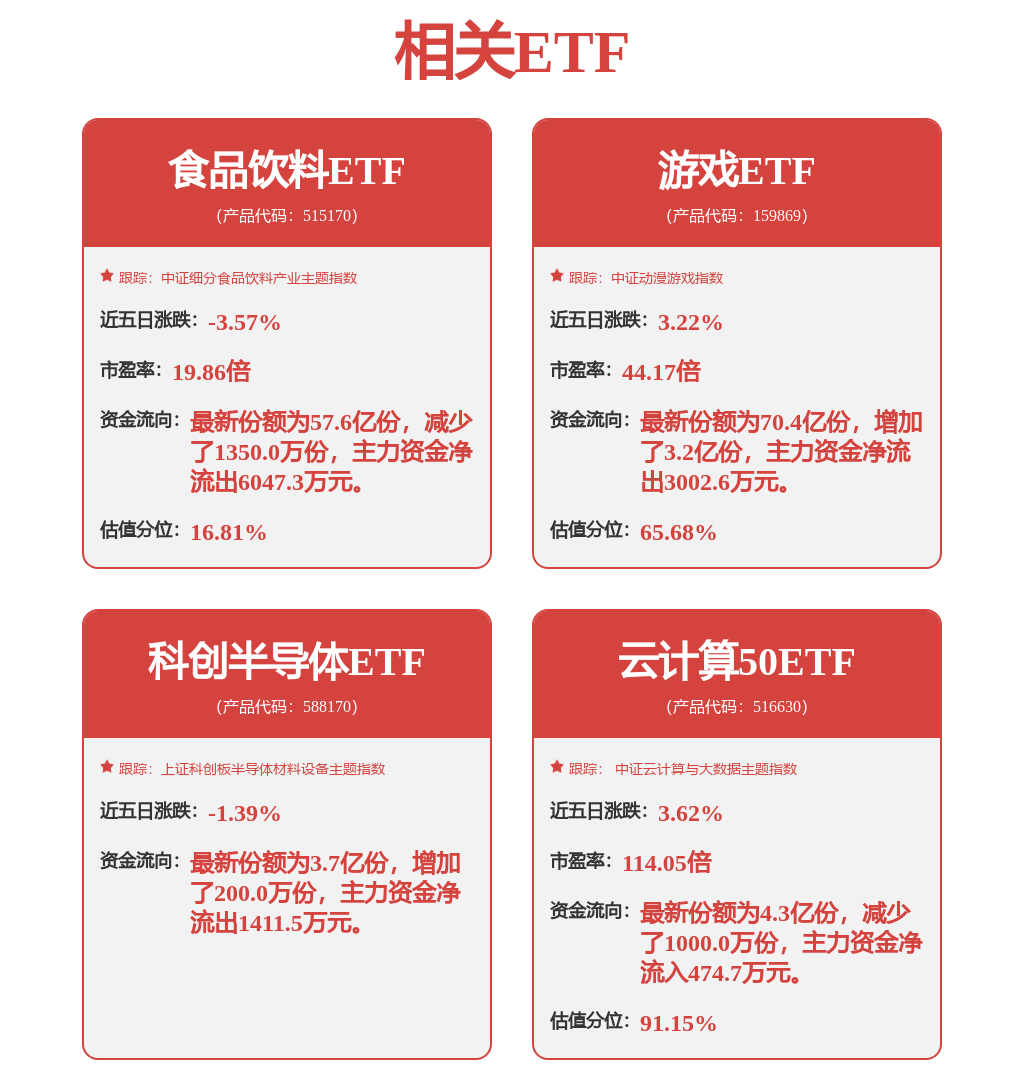
推荐阅读:
【12315投诉公示】贵州茅台新增2件投诉公示,涉及其他人身权利问题等